与此同时,以色列药物警戒专家在当地PFS自杀案的家庭起诉默克公司后,在药物不良反应报告中呼吁进行一场“改革”
2022年9月26日
亲爱的朋友们:
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KSM)的研究人员分析了全球公众对非那雄胺影响性健康的关注,确定PFS“显然是个需要进行干预的问题……”。
这份题为“Global online interest in finasteride sexual side effects (全球对非那雄胺性副作用的关注)”的研究,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otence Research (国际阳痿研究杂志)》上,研究由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泌尿外科首席住院医师Kian Asanad博士领导。
Asanad博士与他的三名研究成员开始研究前掌握的情况是:
72%的美国人在网上查找健康信息,其中77%的人使用普通(非医疗)搜索引擎,如Google…定性数据显示,患者使用网页搜索的健康信息来完成从直接决策到与护理团队指导讨论的一切。了解这些模式可以促进对医患关系的更好理解以及更高的透明度。
然后,为了确定关于非那雄胺及其副作用的全球趋势,他们在Google Trends中插入了术语“Finasteride (非那雄胺)”、“Finasteride Side Effects (非那雄胺副作用)”、“Post-Finasteride Syndrome (非那雄胺后综合征)”、“Propecia (保法止)”和“Propecia Side Effects (保法止副作用)”。
接下来,该团队比较了从2004年到2020年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对每个词的年度总搜索量。
“我们发现人们对‘非那雄胺后综合征’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呈急剧增长趋势,平均(年变化百分比)达+151.7,”Asanad博士写道,并指出2012年FDA要求将以下不良反应添加到保法止处方信息中:“停止治疗后继续存在的性功能障碍,包括勃起功能障碍、性欲障碍、射精障碍和性高潮障碍。”
 在将用于治疗脱发的处方药(非那雄胺)的通用名及其品牌名(保法止)的搜索量与被定义为对人类健康有负面影响的术语名称结合比较时,这种“显著关注”变得更加明显。
在将用于治疗脱发的处方药(非那雄胺)的通用名及其品牌名(保法止)的搜索量与被定义为对人类健康有负面影响的术语名称结合比较时,这种“显著关注”变得更加明显。
以下是2004年至2020年美国搜索量的年平均变化百分比:
• “Propecia (保法止)”:-9.8
• “Finasteride (非那雄胺)”:+ 9.2
• “Finasteride Side Effects (非那雄胺副作用)”:+20.7
• “Post-Finasteride Syndrome (非那雄胺后综合征)”:+29.2
“医学界的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PFS是一种真正的临床症状。我们的……分析表明,PFS显然是一个对公众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干预。因此,这是不容忽视的,”Asanad博士表示。
中东危机
尽管有大量关于非那雄胺与一系列不良健康事件(包括自杀)有关的医学文献可通过数字渠道获取,但世界各地的医生仍然在开这种药时很少警示甚至根本不警示患者。
最近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国家是以色列。上周,圣地(Holy Land)最古老的日报《Haaretz (国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Israeli Victims of Propecia Speak Out: ‘I Woke Up Into a Nightmare (保法止以色列受害者发声:我在噩梦中醒来)》的报道。
罗尼·林德(Ronny Linder)在6700字的特稿中记录了三位以色列PFS患者(均以化名称谓):尤里(Uri) – 35岁,吉尔(Gil) – 42岁,和埃雷兹(Erez) – 4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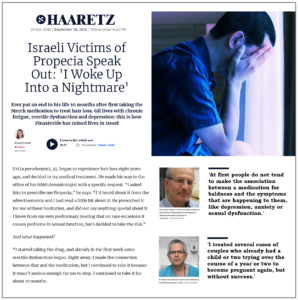 “他毫不犹豫地给我开了(保法止),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尤里回忆起他的皮肤科医生给他诊疗时的场景。当时是2014年。
“他毫不犹豫地给我开了(保法止),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尤里回忆起他的皮肤科医生给他诊疗时的场景。当时是2014年。
“大约10个月后,我的焦虑开始发作,还有脑雾症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没有情感的丧尸,”他继续说道。“然后我告诉自己,可能是药的问题。”于是他就把药停了。但是:
症状并没有消失。我经历了多年的焦虑反复发作,有些时候甚至一天发作几次。我也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抑郁,有过自杀的念头。丧尸的感觉至少持续了6个月。我停下了工作……花了很长时间,身体才恢复一些平衡,但不幸的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在尤里命运多舛的协商之前两年,吉尔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他告诉报社:
我头顶两侧的头发最初有轻微的脱落。我去看了健康维护组织(HMO)的皮肤科医生,问她是否认为这是脱发。她给我做了检查,说是的,如果我再不进行治疗,那么我的头顶最终会变秃……就在这一次预约就诊时,她给我开了保法止(Propecia)……我知道我服用的是激素类药物,我有一些担忧,但医生没有警告我有任何副作用……在我开始服用两三个星期后,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一块夹板插入了我的头。
几周后,吉尔突然戒掉了保法止,结果却经历了PFS患者们所称的“崩溃”:
这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感觉——好像我身体的所有系统都停止工作了。整个身体感觉就像被电了一样…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在急诊室里,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没有做任何激素检查,然后他们放了我,让我回家了。
不久之后,他就被自杀的念头所困扰:
我曾说过很多次。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失去了我的生活。我没能继续我的学业。我没有伴侣……我一点也不乐观。最糟糕的是,我不是一个人,网上有很多论坛,感觉就像进了地狱。很多人都在描述他们在如何努力抗争,努力恢复到曾经的自己……而他们的医生却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
尽管吉尔经历了可怕的事情,但他的情况与第三个PFS患者相比简直相形见绌。2016年5月,在第一次吞下非那雄胺10个月后,埃雷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Haaretz(国土报)》报道,他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直到2015年7月下旬,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乐观、坚强,富有创造力并且非常热情,对我的孩子和我的妻子来说也是一个尽职的父亲和丈夫。我的事业很成功,身边总是围绕着朋友和专业的同事。但从我开始服用一种叫保法止的药的那一天起,一切都变了。回想起来,这种药毁了我的生活……我失去了……我的自我价值感。和身体症状一起,它在我体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挫折以及对未来的恐惧的循环……我尝试了各种改变,因此我决定不再活下去。
据《国民报》报道,埃雷兹(Erez)的遗孀加利亚(Galia)已将默克公司、健康维护组织(HMO)和负责给她丈夫开这种药的医生告上了法庭,状告其没有事先警告风险。
“对我而言,他们在他开始服药的那天就杀了他,”她告诉报社。
大数据来拯救?
还引用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内科专家迈尔·布莱基斯(Mayer Brezis,医学博士)的话,他指出:
对于副作用和一款药之间的因果关系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成共识,而反对者也会在这一过程中突然出现——这些势力通常与这个行业有关。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一开始人们并不倾向于把治疗谢顶的药物和他们身上发生的症状联系起来,医生也不知道者之间存在有任何联系。慢慢地,但肯定的是,报告、研究和意识会增加——从这时开始,显露症状强度和程度的雪球效应就开始了。
布莱基斯博士还认为,目前将药品标签作为患者安全核心的这种模式应该被废除:
说明书是一个笨拙而无用的工具。这是(制药公司)在合法地掩盖自己的问题。人们不会阅读说明,即使他们读了,通常也无法正确理解。当一个人在寻找一种化妆药物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时,医生有义务警告他,这种风险可能会损害他的生活质量……提供药物的医生有义务告知患者相关风险以及治疗的替代方案,这是患者权利相关法律规定的义务……有必要在解释提醒方面进行一场改革。
至于改革会是什么样子,他说:
我们花了20年时间才了解保法止的严重危险……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通过与患者合作,有可能加快这一过程: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用户友好并且智能的在线报告系统……将这些报告与HMO的数据库关联起来,然后通过比较没有服用该药物且具有相似特征的患者,就可以分析副作用和服用该药物之间的联系。
 任何居住在美国并患有非那雄胺后综合征的人都应该向美国FDA报告其症状。任何居住在美国以外并患有非那雄胺后综合征的人都应该向美国FDA以及其当地的药品监管机构报告其症状,正如我们的“举报你的副作用/Report Your Side Effects”页面所示的那样。
任何居住在美国并患有非那雄胺后综合征的人都应该向美国FDA报告其症状。任何居住在美国以外并患有非那雄胺后综合征的人都应该向美国FDA以及其当地的药品监管机构报告其症状,正如我们的“举报你的副作用/Report Your Side Effects”页面所示的那样。
最后,如果您或您爱的人正在遭受非那雄胺后综合征,特别是感到抑郁或情绪不稳定,请不要犹豫,尽快通过我们的患者支持热线联系我们:social@pfsfoundation.org
谢谢!
相关新闻

